怎么對沖疫情和經濟下行?其實最簡單有效的辦法還是基建," 新基建 ",短期有助于擴大需求、穩增長、穩就業,長期有助于釋放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提升長期競爭力,改善民生福利
這幾年,中國經濟分析研究最需要的是客觀專業務實,現在社會上有些思想認識存在 " 一刀切、層層加碼 ",非黑即白是情緒化的民粹的業余的。現在一提到基建有些人就會上綱上線,說是刺激鐵公基,這是嚴重誤解。過去 40 年,沒有適度超前的基建,怎么會有中國制造的強大競爭力?沒有超前的網絡寬帶建設,怎么會有互聯網經濟的繁榮發展?而印度經濟發展潛力釋放不出來,很大程度受制于基礎設施短缺,道路、橋梁、衛生系統都問題很大。
從歷史看,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中國增發特別國債加強基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推出大規模基建投資,盡管當時爭議很大、批評很多,但現在看來意義重大,大幅降低了運輸成本,提升了中國制造的全球競爭力,釋放了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巨大潛力。
啟動 " 新 " 一輪基建,關鍵在 " 新 ",要用改革創新的方式推動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而不是簡單重走老路,導致過剩浪費和 " 鬼城 " 現象。未來 " 新 " 一輪基建主要應有四 " 新 ":
一是新的地區。2019 年中國城鎮化率為 60.6%,而發達國家平均約 80%,中國還有很大空間,但城鎮化的人口將更多聚集到城市群都市圈。我們預測,到 2030 年中國城鎮化率達 71% 時,新增 2 億城鎮人口的 80% 將集中在 19 個城市群,60% 將在長三角、粵港澳、京津冀等 7 個城市群,未來上述地區的軌道交通、城際鐵路、教育、醫療、5G 等基礎設施將面臨嚴重短缺。對人口流入地區,要適當放松地方債務要求,不搞終身追責制,以推進大規模基建;但對人口流出地區,要區別對待,避免因大規模基建造成明顯浪費。
二是新的主體。要進一步放開基建領域的市場準入,擴大投資主體,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項目要對民間資本一視同仁。
三是新的方式。基建投資方式上要規范并推動 PPP,避免明股實債等,引進私人資本提高效率,拓寬融資來源。
四是新的領域。調整投資領域,在補齊鐵路、公路、軌道交通等傳統基建的基礎上大力發展 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智慧城市、數字經濟、教育、醫療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創新穩增長,發展創新型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有觀點認為,大搞減稅基建將增加地方債務負擔、財政收支平衡壓力大,我們認為這種觀點缺少長遠的大局觀,在經濟下行壓力大的時候財政還要保收支平衡將使企業居民雪上加霜,財政應該搞跨期平衡,從平衡財政轉向功能財政。只要中國經濟繁榮發展,人民安居樂業,何愁未來財政問題。如果百業蕭條,財政何談平衡。
還有觀點認為,應該通過控制大城市規模而不是改善城市基礎設施,來治理 " 大城市病 "。我們通過幾十個代表性經濟體上百年城市化歷史研究發現,人口流動的基本規律是 " 人往高處走,人隨產業走 ",都市圈城市群化是未來人口流動的大方向。過去受 " 小城鎮派 " 的 " 控制大城市規模、積極發展中小城鎮、區域均衡發展 " 的計劃經濟思想誤導,導致人地錯配、供求分離,一二線高房價,三四線高庫存。
我記得 10 年 20 年前,就有很多觀點都說北京人口太多了。2000 年北京常住人口 1382 萬人,2008 年 1695 萬人,根據統計部門公報 2019 年 2154 萬人,事實上根據大數據可能已經超過 2500 萬人。20 年前我們按照 1500 萬人規劃了這座城市,規劃了她的土地供應、軌道交通、公路、教育、醫院,現在北京人口增加了 1000 萬人,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樣子。所以,人口流入城市進行適度的基礎設施建設,不僅有助于穩增長,而且是重大民生福音,何樂而不為呢?(來源:澤平宏觀)
這幾年,中國經濟分析研究最需要的是客觀專業務實,現在社會上有些思想認識存在 " 一刀切、層層加碼 ",非黑即白是情緒化的民粹的業余的。現在一提到基建有些人就會上綱上線,說是刺激鐵公基,這是嚴重誤解。過去 40 年,沒有適度超前的基建,怎么會有中國制造的強大競爭力?沒有超前的網絡寬帶建設,怎么會有互聯網經濟的繁榮發展?而印度經濟發展潛力釋放不出來,很大程度受制于基礎設施短缺,道路、橋梁、衛生系統都問題很大。
新基建正在成為朝野共識,是應對疫情和經濟下行的最簡單有效手段
新基建正在成為朝野共識,是應對疫情和經濟下行的最簡單有效手段,是中美貿易摩擦下大國競爭和改革創新的勝負手,不是四萬億重來重走老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3 月 4 日召開會議,會議指出,要加大公共衛生服務,應急物資保障領域投入,加快 5G 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要注重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從歷史看,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中國增發特別國債加強基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推出大規模基建投資,盡管當時爭議很大、批評很多,但現在看來意義重大,大幅降低了運輸成本,提升了中國制造的全球競爭力,釋放了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巨大潛力。
啟動 " 新 " 一輪基建,關鍵在 " 新 ",要用改革創新的方式推動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而不是簡單重走老路,導致過剩浪費和 " 鬼城 " 現象。未來 " 新 " 一輪基建主要應有四 " 新 ":
一是新的地區。2019 年中國城鎮化率為 60.6%,而發達國家平均約 80%,中國還有很大空間,但城鎮化的人口將更多聚集到城市群都市圈。我們預測,到 2030 年中國城鎮化率達 71% 時,新增 2 億城鎮人口的 80% 將集中在 19 個城市群,60% 將在長三角、粵港澳、京津冀等 7 個城市群,未來上述地區的軌道交通、城際鐵路、教育、醫療、5G 等基礎設施將面臨嚴重短缺。對人口流入地區,要適當放松地方債務要求,不搞終身追責制,以推進大規模基建;但對人口流出地區,要區別對待,避免因大規模基建造成明顯浪費。
二是新的主體。要進一步放開基建領域的市場準入,擴大投資主體,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項目要對民間資本一視同仁。
三是新的方式。基建投資方式上要規范并推動 PPP,避免明股實債等,引進私人資本提高效率,拓寬融資來源。
四是新的領域。調整投資領域,在補齊鐵路、公路、軌道交通等傳統基建的基礎上大力發展 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智慧城市、數字經濟、教育、醫療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創新穩增長,發展創新型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有觀點認為,大搞減稅基建將增加地方債務負擔、財政收支平衡壓力大,我們認為這種觀點缺少長遠的大局觀,在經濟下行壓力大的時候財政還要保收支平衡將使企業居民雪上加霜,財政應該搞跨期平衡,從平衡財政轉向功能財政。只要中國經濟繁榮發展,人民安居樂業,何愁未來財政問題。如果百業蕭條,財政何談平衡。
還有觀點認為,應該通過控制大城市規模而不是改善城市基礎設施,來治理 " 大城市病 "。我們通過幾十個代表性經濟體上百年城市化歷史研究發現,人口流動的基本規律是 " 人往高處走,人隨產業走 ",都市圈城市群化是未來人口流動的大方向。過去受 " 小城鎮派 " 的 " 控制大城市規模、積極發展中小城鎮、區域均衡發展 " 的計劃經濟思想誤導,導致人地錯配、供求分離,一二線高房價,三四線高庫存。
我記得 10 年 20 年前,就有很多觀點都說北京人口太多了。2000 年北京常住人口 1382 萬人,2008 年 1695 萬人,根據統計部門公報 2019 年 2154 萬人,事實上根據大數據可能已經超過 2500 萬人。20 年前我們按照 1500 萬人規劃了這座城市,規劃了她的土地供應、軌道交通、公路、教育、醫院,現在北京人口增加了 1000 萬人,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樣子。所以,人口流入城市進行適度的基礎設施建設,不僅有助于穩增長,而且是重大民生福音,何樂而不為呢?(來源:澤平宏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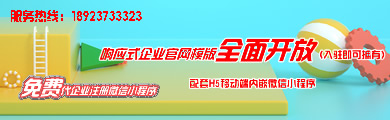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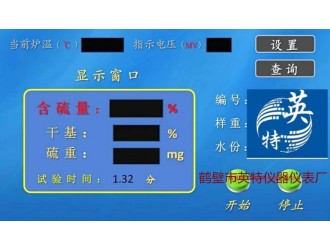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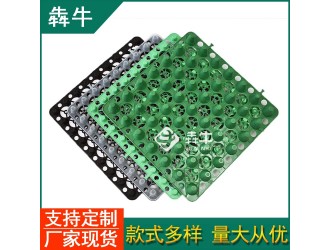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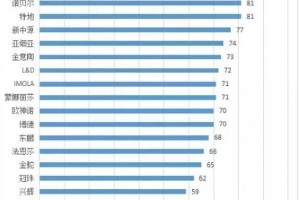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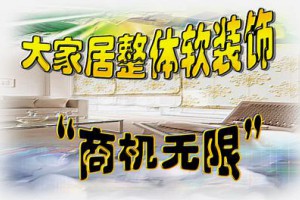








 粵公網安備 44030402000745號
粵公網安備 44030402000745號 